符號載體的保存與延續
符號載體的保存與延續
國際知名駭客組織「匿名者(Anonymous)」曾經在2011年8月10日,利用YouTube的網路空間,以〈Message from Anonymous: Operation Facebook, Nov 5 2011〉做為標題,以摧毀「臉書(FaceBook)」系統做為行動的終極目標,發佈同年11月5日將對FB(FaceBook簡稱)進行攻擊的宣告影片。這段影片公佈數日,發佈訊息的帳號與影像便遭到移除。駭客「匿名者」即將進行的攻擊意圖,以及宣告影片「被移除(抹除)」的現象,凸顯出文字、圖像、聲音等等符碼與數位資訊載體的奇特關係。如果駭客攻擊成功,表示FB伺服器所承載的一切資訊,將遭到全數銷毀;宣告影片與身份資訊的「被移除(抹除)」,也預示著網路伺服器有著更高的宰治者,足以操縱使用者符碼的存在與否。再再提醒所有的使用者,數位時代固然增加了文本「複製」和「散佈」的速度與功能,但是,數位場域依然存在人為的危機和隱憂。光電數位載體的時代,依然無法消除可能被後世「遺忘」的焦慮。
周紹明(2009)《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所介紹的是,西元1000-1800年間中國以紙本、木材做為符號載體,以手抄本、印刷本做為複製形式的時代。在雕版印刷術發展之後,知識複製的速度隨之加快,在明朝中期之後的民間書籍出版產業中,謄寫抄手與雕版刻工的工作分配,有如十九世紀之後工業生產線的作業流程,有著越來越細的分工現象,例如書法字型、筆順部件皆有明確的SOP規格化分配等等。知識複製進入量產階段,並且透過經濟物流、餽贈文化的發展,得以快速散佈。在官方機構方面,亦藉由雕版印刷的生產技術,進行官刻書籍的出版。
知識份子(士人)之間藉由贈與風氣、金錢購買、相互借閱、以物易物、抄手謄寫、資產繼承方式尋求書籍。有些文人雅士基於收藏文物的喜好,廣收珍本、善本書籍,甚至建立私人藏書閣,並且參與書籍印刷出版。出版社與藏書閣儼然成為民間重要的知識保存、複製、傳遞的處所。周紹明便在書中舉出胡應麟(1551-1602,藏書癖)、毛晉(1599-1659,出版家,「汲古閣」創建者)、陳繼儒(1558-1639,老闆編輯家)、顧元慶(1482-1565,編輯家兼出版家)、殷仲春(生卒年不詳,±1596在世,編輯家兼出版家)、童佩(1524-1578,書商、出版家、藏書家)、徐(1570-1654,私人藏書家)等明朝末年特異的藏書家,描述藏書家與出版商的密切關係。
誠如周紹明所言「書的主人傾向於把書視為自己的物品,差不多好像是他們自己的創造物,認為擁有這些書有利於通過高度個人化的傳遞鍊條控制書中知識的傳播」,藏書閣成為知識聚集的處所,具有終端伺服器的保存、複製、散佈功能,藏書家(出版商)同時也擁有把持知識、釋放知識的權力。當知識至高權力的主宰出現財產的分割繼承,藏書閣的管理出現疏漏等諸多問題,都可能造成書籍的離析散亡,致使知識遭到抹除,而無法為後世記憶。雖然周紹明依序列舉了四川孫家(晚唐-南宋初期)、山東韓家(11世紀-13世紀中期)、葉盛(1420-1474)、吳寬(1436-1504)、文徵明(1470-1559)、祁承熯(1563-1628)、蘇州府常熟縣孫家(16世紀-19世紀)、寧波范家(1560-1950,「天一閣」擁有者)等等知識資產成功移轉,得以保存百年的例證。但是,知識典籍在傳遞過程中,仍然無法免除風災、水患、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威脅,遭遇偷盜戰亂、鼠食蟲蛀而造成書籍毀損。後代子孫因應政治考量,甚至可能主動銷毀不受政府機關喜愛的書籍(政治動盪),如果發生管理疏漏,也會造成書籍被偷、私自販售、出借未還,致使藏書閣知識體規模日漸萎縮。知識載體在主宰者的變動中,內容也隨之亡逸。
文明對於知識的複製、保存,始終存在焦慮,諸多自然、人為因素,造成知識的毀損與抹除,讓王明清(1145-1207)、顧炎武(1613-1682)等知識份子極力重建散亡的書籍,試圖保存古代典籍。有遠見的藏書家,明白典籍的散佈與傳遞,才是保存知識的最佳方法,范欽(1506-1585,「天一閣」創建者)、王世貞(1526-1590)達成「知識共享」協議;焦竑(1540-1620)、陳第、趙綺美、徐(1570-1654)、梅鼎祚(1549-1615)亦有書籍往來借閱的互動,避免單一處所的保存系統,擬構「異地備援」儲存系統。
「金石」有時而盡,未若「時空」之無窮,典籍在不斷的複製、散佈而得以延續。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知識加諸於甲骨、金石、竹簡、紙張、硬碟各種不同類型的載體之中,藉由不斷的複製,減低全面摧毀的可能,持續向後世傳遞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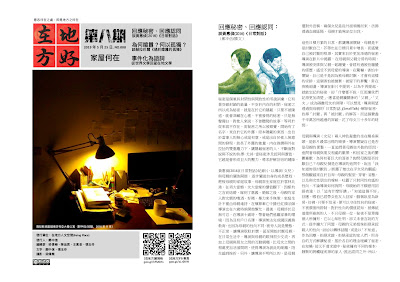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