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林中漫長彌留的死亡時間
向日葵林中漫長彌留的死亡時間
史鐵生(1951-2010)在〈葵林故事(下)〉曾說「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的信仰,和自由的放棄信仰(頁379)」,以向日葵花始終朝向陽光的屬性,進行人類追求信仰、堅持信仰的隱喻,鋪陳了一段遭人歧視、孤立的「叛徒」故事。而這個故事內容,也誠如史鐵生的敘事意圖,可能是那個時代的每一個人都可能經歷的遭遇。不論是堅守信仰或是放棄信仰,在那個批鬥的時代,在成為俘虜的時刻,不是面對結束生命的死亡抉擇,便是面對猶如「業風」的吹拂,進入毫無止境的身體苦痛與精神摧殘。獲得釋放與僥倖生存的俘虜,在脫離囚禁之後,便是進入漫長彌留並且充斥「歧視」、「孤獨」、「悔恨」的靈魂死亡狀態。
因為俘虜必須說出秘密才能夠生存,而秘密會讓其他的人成為俘虜,所以從俘虜身份中生存下來的人,另外被訴諸了「叛徒」的身份。叛徒並不見得是因為放棄信仰而被孤立,而是「殃及」他人而被憎恨。石鐵生對這種「被殃及」的心裡,做了冷靜的描述「憎恨叛徒的人為什麼憎恨叛徒?主要不是因為叛徒背叛了什麼信仰。……主要是殃及。……叛徒,會使得憎恨叛徒的人也走進叛徒曾面臨的那種可怕處境(頁379)」,因此害怕「被殃及」的人群,彼此之間失去了信任,也為了讓不幸被抓的俘虜不再殃及他人,群眾開闢出孤立、嘲弄、歧視的制裁,讓俘虜進入「如果她高尚她就必須去死,如果她活著她就不再高尚,如果她死了她就不能享受幸福,如果她沒死她就只能受到懲罰(頁383)」的荒謬選擇。
更加可怕的是,在「不再高尚」的他者眼光之下,在不再具有人群位置的社會邊緣之中,俘虜加諸於自己「貪生怕死」的道德批判,進入價值觀誖反的「悔恨」,讓「叛徒」潛入自我的存在意識中,怵目驚心的說出「我的罪孽深重,但從未懷疑當初的信仰」言論。落款於葵葉的斷片文字,在僅有六十天生命週期的植物中,讓象徵追求理性之光(啟蒙/Enlightenment)的向日葵林場域隱喻,陷入信仰追求與道德評斷截然的分離,成為誖論問題的迷思。(史鐵生(1995)《務虛筆記》台北:木馬文化,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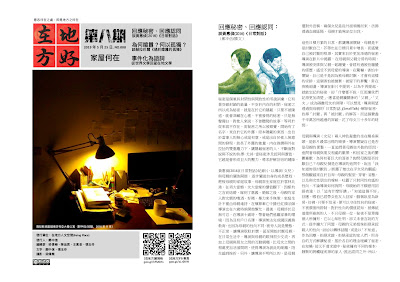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